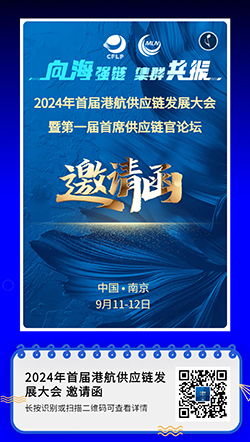从全球氢能格局之变,看中西发展逻辑之辨
氢能发展席卷全球。
近年来,我国氢能产业在交通、工业、能源等多个领域取得显著进展,政策支持、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共同推动了氢能产业的快速发展。2022年,全球首个“碳中和”冬奥会在北京举办,这是一场成功探索氢能源应用的奥运会,氢作为冬奥会火炬唯一燃料,氢燃料电池汽车则成为运输主力;2023年,宁东可再生氢碳减排示范项目50万千瓦光伏实现全容量并网,标志着全国首个集制、储、加、用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可再生氢碳减排示范项目取得重大进展;2024年,上海首个集源、网、荷、储于一体的全闭环零碳氢储工程——安亭镇零碳氢储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启动,标志着通过氢电耦合和清洁能源综合利用的创新技术模式成功落地……
对比我国氢能产业蓬勃发展、欣欣向荣的态势,氢能在西方国家却正在遭遇“滑铁卢”。在美国,特朗普上任首日签署总统令暂停根据《通胀削减法案》和《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》向企业提供绿氢补贴。政策反转给美氢能产业发展带来重大利空,两大氢能中心项目Heartland和MACH2岌岌可危。在欧洲,挪威制氢公司耐欧氢气年初宣布裁员20%并关停核心生产线,法国电解槽制造商Elogen打算卖掉自己,德国公用事业公司Uniper推迟旗舰制氢项目。在澳大利亚,昆士兰州宣布停止向州旗舰绿氢和氨气项目提供财政支持,新南威尔士州猎人谷绿氢枢纽项目无限期搁置,澳能源公司Origin Energy全面叫停旗下氢能开发项目。
是什么拖累了西方氢能发展脚步?政策摇摆不定、支持力度不够。氢能作为一个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,对政策依赖度较高。西方国家政局和政治生态的摇摆性,给氢能企业和项目部署带来极大挑战。
以美国为例,联邦层面针对氢能的政策缺乏连贯性和长期性,尽管部分州积极推动氢能发展,但各州政策支持力度不一,导致市场割裂,难以形成规模效应。加之审批流程繁琐冗长以及监管框架不确定性,投资者难以做出明智的长期决策。
制氢成本昂贵、基础设施落后。一方面,氢生产、储存和运输成本居高不下,难以与传统化石能源竞争。例如,德国虽大力推动绿氢,但电价高企导致成本居高不下。另一方面,加氢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,极大限制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和应用。例如,美国加氢站主要集中于加州城市,覆盖范围有限,影响用户体验。
技术成熟度低、市场需求分散。一方面,氢能产业链技术如电解水制氢、碳捕捉与封存(CCS)技术等,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,制约氢能规模化应用。在美国,得州和加州都通过政策激励推动蓝氢项目,但蓝氢依赖的CCS技术一直受困于高成本且未商业化,美国大部分CCS项目因经济性不足而进展缓慢。另一方面,不同行业对氢能需求差异较大,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驱动力。例如,美国工业领域对氢能需求主要集中在炼油、化工和钢铁等行业,但应用规模较小。
中西方氢能发展态势的分化,凸显出顶层设计的重要性,也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全球氢能产业格局深刻变迁。顶层设计、政策支持、市场驱动、产业协同、能源优势、强大基建……我国在能源战略、产业布局和政策支持等方面的远见卓识,正在推动我国成为全球氢能领域重要参与者。同时也预示着,新一轮能源革命主导权之争已悄然展开。
 微博
微博
 微信
微信
 视频号
视频号
相关文章:
相关推荐: